大盘加速探底 静待趋势明朗
2023-06-06
更新时间:2023-05-25 16:39:18作者:橙橘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泉】
11月14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巴厘岛会晤。中美关系在经历了由于佩洛西访台而造成的严峻局面之后,开始出现一些企稳的积极信号。
这次会晤的时间点发生在中国胜利召开二十大、美国也基本结束中期选举之后,基于目前中美两国的发展规划和态势,可以想见这次会晤的历史意义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逐渐显现。而中美两国在互动中逐渐摸索出的更具操作性的原则、程序和机制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走向。
中美战略互动
抛开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对外战略不谈,就以拜登上任以后的对华政策演变来看,中美直接对抗的风险一度升高。从2021年3月3日白宫发布《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到2022年10月12日发布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两国的国际政治学者都有疑虑,担忧中美是否会步入新冷战。
另外,和以前旧版本的安全战略报告不同,美国这次刻意突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向外界解读安全战略报告时,强调美国会将竞争的关注点放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战略上,而不是要造成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对立。[1]这也难免不让人怀疑美国是否在为制造“一中一台”做铺垫,并且要继承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公开对抗立场。
而在美国最新版的安全战略报告发布后一个月,两国最高领导人就进行了面对面的长时间交谈。美方提出“五不四无意”,中方表示“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这对降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猜疑无疑具有很高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更为重要的是,从会谈后公布的新闻通告来看,习主席将美方安全战略报告的两个立论基本前提都给顶了回去。[2]其一是不同于美方最近几年一直强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方再次强调的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二是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习主席2015年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就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关论述,在巴厘岛会晤中也没有回避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上的差异,并指出“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
从国与国之间战略沟通,释放战略信号的角度来理解,这已经是在求取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希望做到求同存异。
美方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在巴厘岛会晤中的表态,也可以理解为在尽量清晰地释放战略信号。不过考虑到自从2018年“贸易战”以来基本都是美方先手改变现状,美国在主动出击中所遵循的思维模式,可能只会适得其反。
美国的“偏执风格”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战略思维,美国著名学者霍夫施塔特1964年的一篇经典文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介入的视角。
在《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中,霍夫施塔特重点梳理了在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特定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方式影响下反复出现的种种狂热、猜疑、幻想末日对决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大到反对枪支管制,小到反对在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以及美国历史上的反共济会运动,反天主教运动等等。
这种被霍夫施塔特称之为“偏执风格”的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相信一个巨大的外部威胁正在对全体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造成冲击,如果不采取措施果断应对,美国人的世界就会彻底崩塌。如果说临床精神分析中的偏执症患者只是臆想一个在个体层面与自己为敌的外部世界,政治中的偏执思维则会坚持认为这种外部威胁具有整体性和终结性,因此在行动上也倾向于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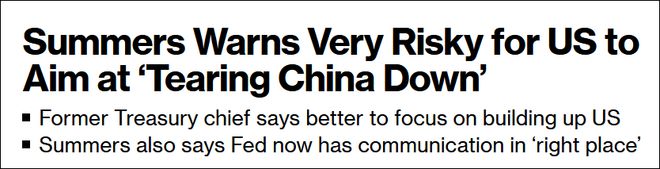

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摧毁中国”的想法是很危险的。
当然,霍夫施塔特也指出这种偏执风格并非美国独有。他当年在演讲中区分了美国、德国、苏联的不同,并认为在美国历史上受这种偏执风格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尤其是自诩为保守派的群体,但其政治代表往往成不了大气候。
可是在60年后的今天,如果说美国政治有什么根本性变化的话,那就是在特朗普当选以及仍然非常活跃的当下,美国主流媒体都一度开始讨论这种“偏执风格”是否会席卷整个社会。[3]
霍夫施塔特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偏执风格”这个概念一般被更多地用于理解美国国内政治,很少被用于对外政策决策分析。只是在讨论诸如历史上的“麦卡锡主义”等问题时,论者会稍微涉及到国际关系层面。所以,探讨这种“偏执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美国具体的对外战略实施还有很大的空间。
国家安全战略涉及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对外部威胁性质、范围和程度的判断,以及对维护自身安全的手段的选择。
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针对如何处理对苏关系曾经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一般认为以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为代表大致形成了鸽派和鹰派两种路线。前者偏重于政治遏制,后者偏重于军事遏制。凯南和尼采二人都是推崇严密理性思考之人,和偏执非理性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从二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冷战实践的过程来看,如果把“偏执风格”理解为对外部威胁的错误定性和目标与手段的错配,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凯南和尼采两人合力之下,在各自影响力的范围之内,推动了冷战的形成。
立足今天回望凯南和尼采的观点、立场,前者从对手国家历史、心理习惯和意识形态立场得出了所谓本质主义认识和“遏制”观点,后者从现实博弈角度出发得出了各种军备竞赛建议,在定义美苏关系本质的源头和互动模式的过程这两方面,通过两者的相互强化而最终形成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几乎将全人类拖入核大战的冷战过程。
苏联当然也有自己的种种问题,但美国作为一直占据优势的一方,需要思考如何避免自己政治文化中的“偏执风格”影响安全战略。在美国社会层面“偏执风格”愈发广泛,“偏执型”政客的影响愈发增强的当下,这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偏执风格”的主导下,会使得对外战略决策忽视关键因素进而导致政策盲点。
“偏执风格”带来的对外政策盲点
首先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前国务卿蓬佩奥开始,美国现在总有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认为美方的各种博弈措施只是针对中国政府,而不是针对中国民众。
但是通过抓捕孟晚舟来打压华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与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作对。用超出正常商业竞争的手段在全球封杀中国高科技公司发展的手法,也是在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作对。
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普通中国民众都希望从国家产业升级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中国的各种龙头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都是产业升级换代的带动力量,打压这些头部企业就等同于压缩所有中国人的发展空间。
虽然从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角度来理解,对技术转移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在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之中无可厚非,但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火候。现在美国因为国内政治气候的原因,在极端政客的推动下,存在进一步将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科技、人文交流泛政治化的倾向。这除了把自己搞成“惊弓之鸟”,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公信力和全球政治稳定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其次,在美国几乎所有安全战略报告中,都会反复提到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拥有全球利益。最新版的安全战略报告基本可以被归纳为一点,两线,四面。焦点是和中国的竞争,两线是美欧、美俄关系,四面是美国在新技术,网络空间,全球贸易,以及全球海域、空域和外太空的规则制定权。
纵观美国自二战以后的对外政策最高目标,核心一点在于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防止任何可以挑战美国的国家出现,无论这个国家具备何种意识形态色彩。
基于对中国发展趋势的预判,美国在奥巴马任内就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首先是奥巴马2009年在日本宣布美国将会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然后在2011年底,几乎同时启动了“转向亚洲”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两项政策。[4]如果这些举措都顺利执行到位,那就不仅可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威慑,还可以将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方向上的经济圈更大一步拉向美国而不是中国。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东京峰会现场
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叫停了“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不仅和中国打起了贸易战,还挑起了和欧洲的贸易争端,最后欧盟在2019年4月15日选择终止“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谈判,反而在2020年12月30日美国国内选战正酣的时点,选择和中国草签了“中欧投资协定”。而且在同一时段内,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北溪二号”开始填充天然气,一旦获得运营许可,即可开始供气。
中、俄、欧三方在欧亚大陆上建立起更紧密的经济关系这一前景,从美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原则来看,堪称地缘政治噩梦。拜登就任之后,这一局面开始扭转。2021年5月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9月“澳英美”三边安保联盟成立,今年2月发布了“印太战略”。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欧洲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至少是大打折扣了。这样在军事和能源上,欧洲只能更加倚重美国的支持;一旦和中国拉开经济距离,欧洲也只能选择和美国形成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
新版安全战略基本上全盘继承了美国二战之后的传统战略实施路径,如果美国可以重新绑定欧洲,大幅削弱俄罗斯,并压制中国的上升空间,那就基本算是实现了报告中的主要目标,就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塑国际制度。但这中间绕不过去的一个政策盲点在于美国的战略规划中似乎总是把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混为一谈。
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经典论断,在今天分析资本与国家关系的时候需要做更细致的区分。从协调不同资本集团的关系以及协调资本和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美国政府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就不会出现艾森豪威尔提醒警惕军工复合体的情况,卡特也不会尝试拒绝建造更多战略核潜艇的建议。
美国资本从牟利的角度可以讲全球利益,但美国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从生存和安全的角度出发需要一个全球利益,以及由美国国内哪一部分群体来承担获得这个全球利益的成本,都是一个很难界定和平衡的问题。和其他大国相比,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实际上是最好的, 生存和安全压力相对而言都是最小的。这种情况下,跟随资本去追求全球利益是否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就是一个在源头上需要厘清的问题。
另外就对外政策实践而言,以自己的利益为指归,纠集仆从国来争霸的思路,历史上并不鲜见,结局也并不美好。美国的战略规划习惯于考虑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趋势,也经常就什么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实现这些利益的手段展开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总能触及问题的本质。
今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也许美国又需要展开一些哲学思考才能重新找到和中国的相处之道。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